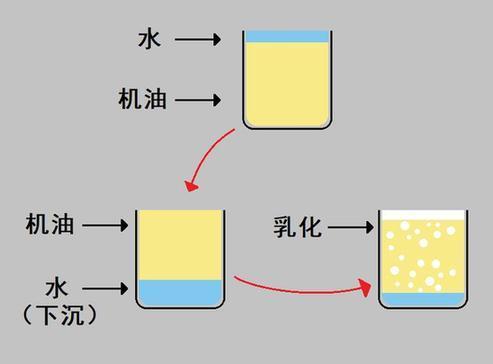□ 熊西平
越往深处走,越能清晰地发现南京的幽。
朱自清先生说,逛南京就像逛古董铺子。深以为然。不过,我眼前的南京,不少地方比朱先生的南京要多一层深绿的锈迹,幽深得多。
南京这古董铺子太大,简直是横在历史架构的多个层面上,阅读它如同盲人摸象。我浮光掠影地走下来,如在初中教科书上读历史,望个框架而已。
离开多日,回首南京,想写点文字,却难。秦淮河、玄武湖、莫愁湖、夫子庙、雨花台、钟山、台城,都被写烂了,至少像一张纸被揉弄得皱皱巴巴。我想,即使排除两千年的风雨侵蚀,仅仅千千万万支大大小小的笔,戳来戳去,金陵也会剥蚀成灰的。文学叹旧,胜过喜新。大概原因就在这里。
等坐在案前胡思乱想,忽然就跑出些似乎与古老毫无关系的猫猫狗狗来。
南京城多猫,是我始料不及的。而且,人家猫都生活在书香庙堂的环境中,更是意外。
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总统府、鸡鸣寺、台城,我都遇见了猫。我对它们印象深刻,不知它们间或一瞥的眼睛里对我这个寻常的匆匆过客是否留下些浅表的印象。
南京大学是我心仪已久的高等学府。拜谒这样的地方,我习惯先要寻觅古建筑,同时凭吊一下历史的天空上不需擦拭却光芒温暖的学人遗迹。
我却意外遇到了多样的猫咪。
南京大学的东园里最可观的是几座亭子和许多六朝的柏桧,树荫浓重,阳光条分缕析地射进来,却晒不干潮湿的阴翳。许多猫就恋在这里。猫们并不肥硕,目光炯炯,很有精神。它们卧在图书馆的台阶上、假山的洞隙里、学生宿舍的窗台上,很从容,宝石般的眼睛在游客身上一转,似乎就扫描到了游客灵魂的影像。
园子里,地质学家李四光赭红色麻石雕像基座上,卧着一只白猫。细细瞅,感觉那猫就是一团毫无杂尘的雪。天还炎热,一团雪让人感到心境格外清凉。
桧树下,建筑学家刘敦桢雕像的黑色基座上,卧一只杂糅了白色条纹的黄猫,散散的样子。它眯着眼,满脸睥睨一切的迷离。我觉得它就是在沉思谜一样问题的古典教授,一点没有谦和的刘敦桢的风格。
来来往往的游客在小径上蜿蜒,多数要驻足雕像旁观看。游人的身影和声音,似乎都被无声地吸附走了,丝毫没有惊动静卧的猫咪。
偶有走动的猫,像一匹黑缎带在飘动,一把夜光在款移。黑猫并不沿着路道走,或在台阶上,或在矮墙上,走走停停,凹一下腰,四周看看。前面是高高耸立的北大楼,藤萝披挂,森然而立。昏黄的夕阳在树间楼间显得有些虚弱,满院子宋元古本的氤氲四起。这只黑猫要去北大楼夜读吗?
每个园子里都有若干造型各异的桧柏,古色苍颜,沉静安详。树上有各种鸟儿毫无顾忌地喧闹,要吵破树的安静,而树并不为之而动。猫呢,也充耳不闻,自顾思考一些千年不解的猜想。
没有匆忙赶路的猫,没有酣然沉睡的猫,没有肥硕如猪的猫,没有骨瘦如柴的猫,没有精警捕食的猫,没有卿卿我我的猫,没有龇牙撕咬的猫,甚至,没有在树上嬉戏作乐的猫。我很纳闷,在这秋老虎淫威下的猫,都是如此状态?猫要觅食的,但是,我感觉这些猫衣食无忧,似乎家里还雇了保姆的样子。
总统府后花园的假山风洞里卧着一只猫,米色。风轻微,不安地在洞里穿进穿出,但丝毫不干扰猫的安静。游人如织,也干扰不了米色猫的白日梦。它只在黑夜里忙活?忙活些什么,没人知道呢,只等着多少年以后渐渐解密吧!
总统府其历史可追溯到明朝的归德侯府和汉王府,后成为太平天国的皇宫,再后来,民国临时政府在此办公。望着风洞里的那只米色猫,我想到了它历史的样子。王府宫女幸福地抱着它走动,王妃远远地向往地看着。一转眼,它就蹲在总统和部长们的餐桌下,一根不剩地拾起鱼刺,津津有味地享用。
夕阳照在鸡鸣寺的塔身和禅堂的屋顶上,温温的,并没有四射的金色光芒。一只肥肥的灰猫趴在僧寮的灰屋顶上酣睡,似乎不知时在何年。僧寮在山腰,我们走的路比屋顶还高。猫就在我们的手边了。我们走路,交谈,对紫金山天文台的指指点点,一点也没惊扰它。这一切似乎是它梦境的影子,而有了影子梦就更沉酣了。正是做晚饭的时间,香集厨的窗子里飘出诱人的香味,我的胃立刻咕噜噜噜地喊出了声。香味飘过屋顶,向着台城和玄武湖的方向走,刚好漫过那只猫。猫一动不动,像旧式屋顶上的一只陶兽。
《中国质量报》

 您当前位置:
您当前位置: